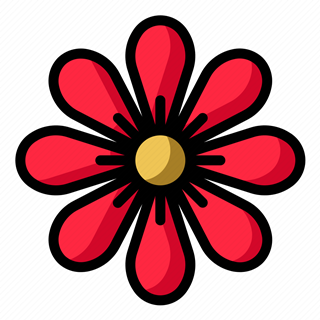在我们赏析一部老电影的时候,往往需要把它还原回当时的历史语境来考察,因为任何电影都有其诞生时期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不过,倘若有的老影片历经岁月,现在看来仍然让人击节赞叹,那必是经典中的经典了。
导演桑弧在1947年为上海文华影业公司拍摄的喜剧片《太太万岁》既是如此。
虽然影片迄今已有七十余载,但影片凭借妙趣横生的情节、出神入化的表演以及工整流畅的镜头语言,在前些年的数次公开重映中总能获得观众强烈的共鸣。
同时,也由于《太太万岁》的剧本出自张爱玲的手笔,让影片在喜剧元素的背后自然地沾染了些许世故和苍凉的情怀。
值得注意的是,20年代末期以来率先对《太太万岁》进行重读阐释的并非电影研究者,而是文学研究者,因此在很多早期的论述中,他们多从文化学或文本的角度来探寻张爱玲的文笔,或多或少地忽视了电影化机制,即低估了桑弧的导演才华。
因此,本文将由桑弧的喜剧技巧先行谈起。
桑弧的喜剧情调
焦雄屏曾指出,《太太万岁》继承了孤岛时期电影的典型特质,它较少触及政治现实,却反映了“中产阶级特有的犬儒和势利观念,门第金钱造成人的隔阂和冷漠”以及在“社会变动中隐隐崩坏却仍在挣扎的道德束缚”。
这与影片的类型选择有着直接的关系。
桑弧
也正是在孤岛时期,原本在银行做职员的桑弧改行进入电影界。他经由京剧大师周信芳而认识了著名导演朱石麟,并很快成为朱导的得意门生。
两人有着同样的爱好,便是特别中意好莱坞导演刘别谦和弗兰克·卡普拉的神经喜剧(也被称为怪癖喜剧),朱石麟轻松、风趣、简洁的导演风格即是经此影响而来,而桑弧后来的喜剧创作亦因此受益匪浅。
神经喜剧是好莱坞历史上的一种特定类型,流行于经济大萧条之后的30年代。而刘别谦和卡普拉在导演手法的处理又各有千秋。
刘别谦的资历相对更深,从1919年的《牡蛎公主》开始,他已经尝试在作品中展现出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幽默感,并通过栩栩如生的对话表达出来。
后来这种手法被尊称为“刘别谦式的情调”,即把构思和人物处境凝练地放置于单个镜头或短暂的场景中,由此对角色以及整部作品的意义起到某种反讽的效果。
卡普拉则是神经喜剧类型真正的奠基者,他赋予了这种类型十足的民粹主义情调。譬如在其代表作《一夜风流》中,男女主角来自不同阶层,他们的性格冲突背后代表着不同的社会态度和行为规范,而他们最终的结合成为力求调解大萧条时期被加剧的社会阶层矛盾的有效手段。
美国电影学者托马斯·沙兹由此评价道:
“这部电影认为如果劳工阶级与娇宠的女继承人可以克服他们在意识形态上的差异而互相拥抱,那么我们就不应该对无产阶级乌托邦社会——或者,至少不同阶级的人可以相互接触的社会——的传统美国理想失去信心。”
从表面上来,《太太万岁》确实与神经喜剧的特点有几分相似。
影片中,富家女陈思珍(蒋天流饰)嫁到一户中产阶级家庭中做太太。她为了支持丈夫(张伐饰)办实业,从父亲(石挥饰)那里“骗”来一笔钱做原始投资;可丈夫有钱之后,却又在外面包起了“小公馆”。
就是这样,思珍在一个大家庭里周旋于各种人物之间,本想到处讨好,却到处不讨好,演出了一幕上海典型的里弄主妇的悲喜剧。
在这个故事中,具备来自社会不同阶层的男女主人公(欢喜冤家模式),有快速迸发、趣味盎然的对白,有脾气古怪、神经质的人物形象,有复杂的三角恋爱关系,有对性克制而隐晦的描写(无性的性喜剧)。
影片最后,经历一场风波的夫妻俩虽然和好如初,但这个喜剧的结局并不十分完美,而最多只能算是个“妥协结局”。
正如好莱坞很多神经喜剧的结尾,男女主角虽然重新结合了,但是他们的紧张关系事实上并没有得到实质性的改变,又回到了原点。
只是通过了一系列的事件,让他们更好地认清了自己并“认命”罢了。
不过从深层结构上说,桑弧最多只是拿来了神经喜剧的壳儿,却没有把这种类型的内核——讨好大众的民粹主义、阶层融合和乌托邦式的社会理想——一并拿来。
桑弧并没有为影片设计一个传统的皆大欢喜的结局,甚至在片中也没有提出任何化解夫妻矛盾的方法。
虽然影片因为喜剧因素引人入胜,但更耐人寻味地在于片中对中产家庭普遍矛盾的揭示,如婆媳矛盾、亲友势利、见异思迁等。
这些都是中国20/30年代以来家庭伦理情节剧经常涉及的主题。
因此,回顾《太太万岁》,以及桑弧同时期创作的《不了情》《哀乐中年》《假凤虚凰》(编剧),我们可以发现他所最为擅长的,正是神经喜剧与家庭情节剧巧妙融合,使得影片既有传统的两性冲突和家族矛盾,也在其间夹杂着善意的嬉笑、反讽与嘲弄,于一种不愠不火的情绪流转间自得境界。
电影技巧与世俗表演
从影片的电影化技巧来看,《太太万岁》堪称教科书式的范本。
这不仅体现在影片的环环相扣、高潮迭起的编剧技巧,同样也在于简洁流畅、意味隽永的视听语言上。
在此需要强调的是,我并不赞同把《太太万岁》的编剧和导演割裂开来看待,张爱玲和桑弧在这部作品中不是各自为战、各顾一摊,尤其对于桑弧而言,他要将张的文字创作用高度洗练的电影语言“转述”出来,更加需要过硬的改编取舍能力。
至于他是否真的对张的剧本做过改动,由于《太太万岁》的原始剧本没有保存下来,今天我们无从知晓。
但只要我们留心,便会发现即便在桑弧晚期的喜剧作品中,仍然可以发现与《太太万岁》相似的技巧,譬如对误会、巧合、讽刺的熟练运用,我想正是基于一种艺术默契,才促成了《太太万岁》这部在编剧与电影化技巧高度水乳交融的杰作。
我们首先还要从影片的类型设置上考察。
正如前文所言,桑弧受刘别谦和卡普拉的影响,在《太太万岁》借来了神经喜剧的类型框架。
这种喜剧形式吸取了舞台剧的滑稽元素,表现出与舞台剧的亲缘性。
《太太万岁》的场景十分简单,主要包括思珍婆家、思珍娘家、咪咪家、志远公司、咖啡馆、律师行以及果品公司、首饰店铺、机场等等。
这当中绝大多数都是内景,而且多是由语言串联起情节发展,因此堪称中国早期的室内情景喜剧。
考虑与此,桑弧在为这个高度戏剧性的作品设计镜头时也多采用了低机位的全景(人物多为全景镜头,仿佛我们正在看一出话剧似的)和半身的中景,辅之于极个别的特写和大远景。
这种四平八稳的构图方式在30/40年代的好莱坞电影中也是十分常见的,随着日后镜头强化和叙事节奏的加快,稳定的全景叙事已经越发稀少。
在叙事上,《太太万岁》采用了很多巧妙的技巧来构成矛盾冲突。
一种是误会,如思瑞(韩非饰)要去给思珍的婆婆(路珊饰)拜寿,依姐姐的吩咐去土产公司买菠萝,恰好思珍的小姑子志琴(汪漪饰)也抱着同样的目的去买菠萝,两人间由此发生了小小的口角。
另一种技巧是巧合。譬如思珍怕婆婆担心儿子安全,谎称志远是坐船去的香港,偏不巧第二天报纸上突报海轮失事、旅客无一幸免,活活把老太太吓得半死。
第三种技巧是对比。影片的主线是思珍与志远的两性冲突,但是在主线外作者还加上了另三条平行关系:思瑞与志琴的自由恋爱、老爷子与交际花的逢场作戏以及拆白党“哥哥”(程之饰)对咪咪(上官云珠饰)的敲骨吸髓。
这些两性关系在当时极具社会代表性,通过潜在的对比展现人情五色冷暖,也在娱乐中令观众良久回味。
还有一种技巧是夸张与噱头。《太太万岁》的幽默感很多时候来自于适当夸张的表演,譬如思瑞在女性面前的自我吹捧,还有老爷子结识交际花后得意忘形的精心装扮,都堪称片中精妙绝伦的华彩段落。
在影片的段落过渡上,桑弧大量地使用了好莱坞的连续性剪辑,这是最符合受众心理的剪辑方式。
譬如在展现茂远公司的发展壮大时,桑弧没有多费口舌,只运用三个招牌的叠化镜头,加摇镜头最终定格在总经理办公室上,显得十分自然流畅。
“同物换景”的古典剪辑方式也在片中多次出现。譬如老爷在在咪咪处拿走登有志远被骗的报纸,待镜头推近换景后,他已然置身女婿家催债了;还有思珍在摆平咪咪后,如释重负地擦汗,同样的动作待镜头从中景拉开时,观众发现思珍已经回到了家中。
除了剪辑外,桑弧还特别注意镜头内在含义的挖掘。他在影片中对于特写镜头非常谨慎,但一旦使用时,譬如对那个别针的特写(今天我们看来会更像广告植入),那便意味着围绕这个物件将要发生的一场三角斗争。
影片后段,志远不惜以手表为代价换回这个别针时,亦表现了男性对感情背叛的救赎,这段戏十分巧妙地借鉴了默片的形体表现方式,通过音乐音响衬托和画外空间的开拓来传情达意已实现反讽的效果,是桑弧借鉴刘别谦手法的最初图体现。
除了编导技巧外,《太太万岁》的成功还离不开演员们的出色发挥。这部剧几乎囊括了当时中国最好的一批话剧演员。
焦雄屏曾给予他们极高的评价,说他们“无论是喜剧的节奏感、表情的夸张感或含蓄细节,或是语言本身的训练,都不下于凯瑟琳·赫本、卡莱·葛伦,或是詹姆斯·史都华。”
耐人寻味的是,他们在这部世俗喜剧表演得是那么的活灵活现,可到了新中国成立后,除了生如夏花、灿烂一时的石挥,几乎都很难融入到工农兵主题的新电影创作中去,因而再也没有复现《太太万岁》的辉煌。
很多人就此被历史埋没了,如饰演志琴的汪漪,《太太万岁》时是多么的美丽动人,然而当她四十年后在《黑炮事件》出演那个古板、令人生厌的马列老太太,我们还能否再忆起她过往的风华?
或许只有她在《黑炮事件》结尾的高楼上口吐眼圈的一瞬,还能让人模糊地忆起一丝海上花的旧时神韵吧。
张爱玲式的苍凉
提到《太太万岁》,必然还要提到张爱玲的人生。
很多研究者已经指出,《太太万岁》在喜剧的表层之外,更负载了一份意味惆怅的无奈感怀。
这显然是和编剧张爱玲个人的心境和情感遭遇有关,在与胡兰成的婚姻挫败后,她“一人雨中撑伞在船舷边,对着滔滔黄浪,伫立涕泣久之”。
而片中思珍的矛盾处境,似乎就是她个人的写照。
纵然是狐媚多情的咪咪,在她屡屡虏获“猎物”,在半遮的香扇后巧笑盼兮时,我们仍然要为其日后即将遭受的、无尽的精神肉体摧残感到惋惜和悲哀。
从某种角度上说,把玩精美香扇的咪咪和手持简陋蒲扇的思珍有着共同的烦恼和悲哀,她们似乎都印证了张爱玲的一句名言:“生命是一袭华丽的袍,爬满了虱子。”
这在影片结尾的离婚段落体现地尤为明显。
香港电影学者郑树森在分析这个十分吊诡的结局时,曾有重要论断:
“陈思珍这位‘贤妻’所代表的‘女权/母权’临危受命,挺身而出,化解危机,浸浸然取代了唐志远的‘男权/父权’。”
这一观点后来也被陈子善、焦雄屏等学者接受,他们发现《太太万岁》中的女性大都是主动和站在支配地位的。
相形之下,志远、思瑞和石挥饰演的老爷子都是被女性操控的角色,传统的男权已经软弱不堪了。
但事实上果真如此吗?我们如何来理解《太太万岁》中思珍一直位于主动,捱到离婚签字却又让志远翻身站了上风的突兀结局呢?
我想,我们还是需要在张爱玲一贯的文字世界中寻找答案。
1944年初,在结识胡兰成之前,张爱玲在名为《论女人》的文章中还透露着一丝高贵的骄傲气:“我们得承认,非得要所有的婚姻全由女子主动,我们才有希望产生一种超人的民族。”
但她也承认,无论女人多能干,“我们的文明是男子的文明......在任何文化阶段中,女人还是女人”。
待到1945年1月,此时张胡已秘密结婚但被迫分居,张爱玲在《气短情长及其他》一文中已经开始透出一丝小女人的不安与无奈,她也并不知道自己的夫君在武汉此时已和另一个女人打得火热。
张爱玲
到了1947年,对爱情绝望的张爱玲终于下定决心与胡兰成诀别,正是在这种心态下她创作了《太太万岁》的剧本,她的心绪也明明地写在这部电影的创作手记中:
“中国女人向来是一结婚立刻由少女变成中年人,跳掉了少妇这一个阶段。陈思珍就已经有中年人的气质了。她最后得到了快乐的结局也并不怎么快乐......我非常喜欢‘浮世的悲哀’这几个字,但如果是‘浮世的悲欢’,那比‘浮世的悲哀’其实更可悲,因为有一种苍茫变幻的感觉。”
张爱玲似乎一下老了,她的文字充满宿命的灰色和无常的漂浮感,她委屈却也无奈地接受了现实。
颇为讽刺的是,为了接济逃亡中的胡,她仍然把《不了情》和《太太万岁》的稿费30万元全数寄予了他。
因此我认为,绝不能因为《太太万岁》中女性绝大多数时间处于支配地位,便简单化地得出女权取代男权的结论。
恰恰正是在影片结尾,志远有意无意地反戈一击中,猛然间改变了整个叙事的走向,从而描绘出女性真正的脆弱悲哀,这也正是伤痛中张爱玲的真实心境写照。
银幕上的思珍因为丈夫的归来破涕为笑,而现实中的张爱玲却于笑中掩埋了更深的悲哀。
我们发自内心地为思珍高兴,也无可奈何地为张爱玲叹息。
即便时至今日,我们仍然可以从《太太万岁》中找到些许现实的影子,这也许正是张爱玲的伟大敏锐之处——借用海外华人电影学者傅葆石的一句评价:
“她被摒弃了,但她的《太太万岁》却把她最熟悉的上海变成不朽。”
后记
由于张爱玲和胡兰成的关系,让《太太万岁》尚未诞生便屡遭舆论界攻讦,也让张爱玲与桑弧这对黄金组合的合作走到终结。
原本两人还期望将张爱玲的代表作《金锁记》搬上银幕,依旧聘请蒋天流饰演女主角,但最终未能成行。
桑弧在新中国成立后留在了大陆,1950年他在“文华”拍摄了故事片《太平春》,虽然仍然以石挥和上官云珠出演,但风格和艺术旨趣已与《不了情》《太太万岁》时期的创作手法相去甚远,反映出电影业从大众消费向政治宣传转变的趋势。
“十七年”是桑弧在新中国电影史上最辉煌的时期:他导演新中国第一部彩色戏曲故事片《梁山伯与祝英台》、第一部彩色故事片《祝福》、第一部彩色宽银幕立体电影《魔术师的奇遇》。
桑弧从来没有忘记喜剧创作,“文革”后老骥伏枥的他接连创作了《她俩和他俩》、《邮缘》、《女局长的男朋友》等等,这些轻喜剧中的很多艺术手法都能让人依稀感受到桑弧在早期创作中的特点。
桑弧十分重视电影的娱乐性,他认为“搞喜剧就要理直气壮地运用噱头,讲究噱头”。
张爱玲则在1952年离开大陆来到香港,后在挚友宋淇的安排下进入电懋公司做电影编剧。
与那时很多的香港电影公司相仿,电懋公司在制片过程中延续了“文华”公司的中产都市喜剧传统,将南迁而来的上海电影文化与香港本地的岭南文化相融合,使得张爱玲的写作才华觅到用武之地。
在她为“电懋”创作的十部作品中,大多数都是都市喜剧。
其中一种是延续《太太万岁》神经喜剧风格的都市浪漫喜剧,如《情场如战场》和《六月新娘》,另一种是表现沪港文化交融的所谓“现实喜剧”,如《南北一家亲》和《南北喜相逢》。
郑树森曾高度评价她的作品道:
“张爱玲这两类剧本相当难得。在当年中国大陆提倡‘工农兵文艺’、台湾高呼‘反攻复国’的文化大气候里,‘都市浪漫喜剧’也只能幸存于英国殖民地的香港。而‘现实喜剧’里的族群问题,在二·二八后的台湾,恐怕很难以谐趣和通婚来一笑置之,自然不会有香港抢拍跟风的现象。”
1964年后,张爱玲的电影生涯宣告结束,但在其后的漫长数十年中,她的文学作品和她的传奇人生仍然是影视改编最为偏爱的主题之一。